千亿体育官网报道
千亿体育_千亿体育官网_千亿APP_千亿体育平台(www.qytygw.com)会员自助返水最高28888元,千亿宝贝等你撩
球盟会-球盟会官网-球盟会体育是亚洲老牌娱乐平台(www.qmhtyw.com)最好足球投注平台,开户送88元,美女宝贝空降!
龙8国际-龙8国际官网-龙八国际娱乐官网-龙八国际娱乐下载(www.l8gjw.com)全球最佳老虎机平台,每日存款送3888元!
乐虎国际-乐虎国际官网-乐虎棋牌游戏官网-乐虎体育app下载(www.lhgjgw.com)真人百家乐连赢,最高88888,让您喜上加喜!
小说:末日游戏:我在洪流中求生存
类型:小说推荐
作者:沈客
角色:陆远我叫明瑶
热门新书《末日游戏:我在洪流中求生存》是由著名网文作者“沈客”所著的小说推荐分类小说。文章简述:灶房里趴了个皮包骨头的人,那是四妹,她正趴在灶边,朝里塞枯叶、吹风,灶上的破锅里煮着一锅沸肉汤。”四、四妹……”四妹转过头,一脸恐惧地朝他拼命摆手。”莫喊,姨哥,莫喊,我分你,我分你一条腿。”年嘉禾咽了口酸水
评论专区
当医生开了外挂:作者把轻佻逗逼当成了轻松幽默,看多了让人恶心。
我是至尊:“ 是堆积如山的玄兽肉。一阵阵异香扑鼻。只是,这分量也太多了一些。 粗略看去,四五十斤是有的。”四五十斤就“堆积如山”,杀一头肥猪得多少山
重生之风流仕途:惊闻

第 1 节 太岁
外边突然传来一声稚嫩的凄叫,把年嘉禾猛地惊醒,还没等他起身,那惨叫声就迅速萎弱了下去。
他撑起身,爬下茅草床,杵着木棍,拖着浮肿的腿,摸到门边扒开条缝,朝外瞄了一眼,巷里没人。
不是路倒。
但不远处四妹家的院子里正传来有规律的劈砍声,过了一阵,袅袅白烟从那里升起,竟有一阵肉香味顺着冷风飘了过来。
年嘉禾肚里猛一颤,肠胃咕噜蠕动着,呕出了一小口酸水。
他只觉得本来薄似纸、透似纱,风一吹就能飘起来的身体,竟被那香味勾得稍稍有了些重量。
他推开门,一颠一瘸地走到四妹家,敲了敲门以后,便忙不迭地推开。
灶房里趴了个皮包骨头的人,那是四妹,她正趴在灶边,朝里塞枯叶、吹风,灶上的破锅里煮着一锅沸肉汤。”
四、四妹……”四妹转过头,一脸恐惧地朝他拼命摆手。”
莫喊,姨哥,莫喊,我分你,我分你一条腿。”
年嘉禾咽了口酸水。”
……你这煮的什么肉?
老鼠都没了,你煮的什么肉?”
四妹用黢黑的手抹了把脸,喜不自禁地说:”猪崽子!
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了一只猪崽子,饿得走不动了,我把它抱住了,一把就抱住了!”
年嘉禾凑近那锅沸腾着的汤,睁大眼仔细看了看,哆嗦着腿往后退一步。”
这不是猪崽子。”
”不、不是猪崽子?
怎么会呢?”
四妹呆滞地喃道。”
我抱住它了的啊,我真的抱住了,好大一只,不是猪崽子,还能是啥?”
”这是家兴。”
年嘉禾说。”
家兴?”
四妹的脸上露出茫然而迟钝的表情。”
家兴是谁?”
”是你的娃。”
”……”过了好几秒,都没有回应,年嘉禾不得不抬头看向四妹。
她仿佛生了根一般,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,那份茫然迟钝的表情硬邦邦地凝固在她脸上。
枯叶在灶里噼啪作响,沸腾的开水溢出锅子,淌在血淋淋的灶台上,四妹依然毫无反应,仿佛变成了一尊泥塑。
年嘉禾转过身,慢慢走出四妹家。
过了几秒,他听见背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凄嚎。
第二天,腐臭味顺着风飘了过来,年嘉禾拄起棍走过去,推开灶房门,四妹倒在地上,没了气息。
他早已没了挖坑的气力,只得用茅草与破布给她草草盖上。
当晚,对面还是响起了凌乱沉重的脚步声,以及刻意压低的说话声。
年嘉禾知道那些人是在干什么。
他没有余力去制止。
大旱已经持续了两年多。
第一年,就几乎颗粒无收,连土豆都闷死在了地里,没能抢出来一块。
县里倒是早早发了赈灾粮,可层层克扣下来,发到手上就只剩下一小袋掺了糠和沙的麦子,还不够煮一锅粥。
靠着存粮,年家村熬过了那个严酷的冬天,只走了几个老人。
第二年开春,倒是下了几场好雨,雾凇挂满枝桠,颇具丰年瑞兆。
可惜二月之后焦旱再至,麦苗还没抽穗就死了十之八九。
火上浇油的是蝗也来了,铺天盖地刮过去,将残存的苗也吃得一干二净。
赈灾粮没了,粥厂也没人开了——别说是县里,就连直隶都已经没粮了。
从那时开始,大饥荒便真正降临了。
年嘉禾依然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的每个日夜——因为每天晚上,都至少会有一家传出哭声。
那就代表又死了一个。
到后来,连哭声都变得低微而压抑——怕人循着哭声,翻进屋里抢尸体。
饿啊。
饿得人根本挪不动窝,说不出话,只能平地躺着,像数数一样地进气、出气,像是给自己的命作倒数。
有力气逃难的基本都逃光了,壮实的、年轻的、有点家底的。
年嘉禾没跟着逃难,他天生跛足,知道自己逃不远。
喜穗也没逃。
无论他怎么劝、怎么骂、怎么赶,她都没逃。
她熬过了冬天,是在开春后咽气的。
她咽气的那天,正好是最后一波蝗飞走,年嘉禾从寸草不生的田里回到寂静无声的家,才发现家里的喜穗也没了。
她弥留那几天,一直在半清醒半迷糊地呢喃。”
嘉禾……去找蛇。”
”找蛇?
找蛇干什么?”
”去找蛇……蛇多的地方有泉眼……”有泉眼兴许就能打出井,打出井来就能灌田了。
喜穗至死都在惦记这个。
可她哪知道,别说蛇,就连老鼠、蚯蚓、蟑螂,都已经被吃光了。
她是闹粤匪时从南方逃难过来的,这些年跟着他,基本没过上几天饱日子。
年嘉禾一声也没敢哭。
他用草席把她包好,埋在了院前的大榆树下面。
榆树的树皮早已被扒光,但枝桠上还在倔强地发着芽,本来再熬个把月,她就能吃到她最喜欢的榆钱儿。
熬吧。
年嘉禾呆坐在门口,望着眼前的漫漫黄土。
等熬过这段旱,看老天爷能不能赏脸,下两场雨,补种点芋头、土豆下去,好歹能收点粮。
好歹能活下去。
活下去干啥呢?
年嘉禾茫然地望着荒村。
往年他是根本没时间去思考这种问题的,他要忙着打秆、松土、施肥、除虫、引水、割麦、打谷……一年到头都忙得像个陀螺,根本停不下来。
哪怕到了冬天,能歇息一下了,心里想着的也是来年啥时播种、存粮够不够吃。
光是活下来就已经足够艰苦了,根本没时间想其他的。
可到了如今,在这数着数儿进气出气的关头,年嘉禾反倒有闲暇思考了。
活着到底图个啥呢?
传宗接代?
光耀门楣?
一阵睡意袭来。
年嘉禾使劲摇摇头,用力揭开快粘住的上下眼皮,他知道要是在这会儿阖眼,很可能就永远也睁不开了。
他不知道活着到底图啥,但他本能地想活着。
远处的干涸河床里,有个缓缓蠕动的黑影,像是条快晒干的蚯蚓,年嘉禾睁大眼仔细瞅了瞅。
是丰登,他弟弟。
这种时候还能有力气在外走动的也不剩几个了,丰登便是其中之一。
丰登匍匐在地上,像蚯蚓般一寸一寸地挪着,他正在龟裂的土块里翻找虫子与树根。
他也已经瘦得跟骷髅一样了,颧骨如两座山一样暴突高耸,眼窝与面颊却如深潭般凹陷,枯皱黯淡的脸上,唯有两只眼珠子亮得吓人,泛出红光。
年嘉禾打个寒颤,他想起了昨晚的事。
偷尸抢尸早已不是新鲜事了,有更恐怖的传言说,附近山中的粤匪残党正在拦路劫杀活人。
丰登从小就是个顽劣的孩子,不干农活,也不读书。
他们原本一起住,但他手脚不干净,偷家里的东西,年嘉禾一怒之下便将他赶出了屋。
那之后他便游手好闲,东家讨一顿饭、西家讨一顿打地混世度日。
这场奇荒降临后,年嘉禾本以为他会是最先熬不住的那批人,但没曾想,丰登的身体里迸发出了一股奇异的生命力,在这干裂的大地上比谁都更努力地挣扎求生。
就像条蚯蚓一样。
——他这么努力地活着,又是图些啥?
这时,一道白光忽地从天空划过,年嘉禾抬头看时,那光已经烈烈灼目如第二个太阳。
再眨眼时,光又不见了,只在天上留下一道辣眼的白痕子,紧接着远处的山坳传来一声炸雷般巨响,把年嘉禾从门槛上猛掀倒在地。
他哆嗦着爬起身,望向巨响传来的方向,只见那边山坳深处正缓缓袅出黑烟。”
这……这咋回事?”
天上咋掉了个太阳下来?
他正欲仔细看,只见下面的丰登爬起了身,顺着河床朝黑烟飘出的山坳走去,年嘉禾瞬间激出了一背心冷汗,朝弟弟的背影用力喊:”丰登……别去!
你个寡货,别过去!”
可丰登压根听不见,丢了魂似的兀自走着,他只得竭力撑起身子,一瘸一拐地追上丰登的背影。
天上的太阳光照下来,他只觉自己纸一样的身躯被照了个透亮,脚步竟有些轻盈起来了,仿佛稍一踮脚,就能轻飘飘地飞起来一样,他就这样跟着丰登,两人一前一后,一脚深一脚浅地摸进了那山坳,踩着碎石,小心翼翼、连滚带爬地滑下斜坡,往那黑烟袅起的地方望去。
焦金流石的河床**,凹下去一个两三米宽的大坑,坑的**是一个石磨大小的土丘,土丘外围是向四周翻开的泥土,里面混合着被烧黑的杂草和枯根,散发出难闻的糊味。
丰登从泥土里拨出一截没有彻底烧焦的树根,草草擦了下以后,就塞进嘴里,混合着唾沫咀嚼吞咽了下去。”
别吃!
你个挨刀货!
有毒怎么办!”
年嘉禾有气无力地骂了两句,试探着朝焦坑**的土丘走去,坑里的土还很灼热,阵阵散发着热浪与白烟,年嘉禾只走了一步,便觉得自己鼻孔都快冒火了,没敢再靠近。
他总觉得那堆土在缓缓地颤动。
不知道是不是热浪导致的错觉。
他捡起一根枯枝,小心翼翼戳了戳,土丘猛地一个震颤,从顶端抖落了不少焦土。
这次绝对不是错觉。
他抹了抹虚汗,用力再捅过去。
大量焦土随着抖颤从”土丘”身上抖落,年嘉禾扔掉树枝,倒退着坐倒在地——他从土丘的内部,看到了一只紧盯着他的眼睛。
丰登走到他身边捡起树枝,把”土丘”上剩下的土层扫掉,随后和年嘉禾一起坐倒在地。
土丘里面是一团磨盘大小,灰白底色,遍布赫色纹理的块状物体。”
……肉?”
丰登颤声道。
那的确像是一块肉。
而他看到的眼睛,就是那坨肉上唯一的器官。
2”造孽——造孽啊!”
背后传来拉长的凄嚎。
二人转头看去,见到一名穿着褴褛长衫的黑瘦老头。
那人是村里的教书先生,孟秀才。
孟秀才其实不算真秀才,他没中过功名,一辈子都只是个老童生。
但他好歹是村里为数不多识字的人,办过几年塾,逢年过节帮人写对联、家书之类,因此村里人都愿尊称他一声秀才。
只不过他终年无法进学,落了心疾,又沉迷起黄老、命理之类偏门学问,便常有些疯癫的举止,常在口里念叨着些”天地玄黄”之类的话四处游荡,村里人都不怎么敢接近他。
他也是大荒来临后,还有力气在外走动的人之一,他仍穿着那件皱巴巴的长衫,因消瘦而暴突的双眼像金鱼一样鼓瞪着,用鸡爪手颤巍巍地指向坑中的肉块。”
造孽啊,你们俩!
你俩闯大祸啦!
你们俩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啦!”
年嘉禾闻言猛一激灵,回头看向肉块。”
秀才,你……你说这是什么?”
”太岁!
是太岁爷啊!
是神仙!
那天上的太岁星君,在黄道太虚上遨游,每至一星次,就在对应的地面上降下一尊太岁爷来。
你们两个挨刀货,刚才干了什么?
你们竟然用棍子在太岁爷头上扫土!
你们冒犯了神仙,整个村子都要跟你们一起遭灾啦!”
年嘉禾不禁心中悚然,转头看了看丰登,也面色发白。
太岁爷降灾的说法,他以前确实听长辈们说过,说有人挖出了太岁,又惧而填埋,导致兄弟妻儿数日内悉数暴毙,他一时间也没了主意,只能眼巴巴地望向孟秀才。”
秀、秀才,那……那我们该怎么办?”
孟秀才转着鼓突的金鱼眼,低头思忖了片刻。”
不管怎的,咱先得把太岁爷好好供奉起来,兴许能让它不降灾祸!
我想想……这星君五行属木,按相生之理,得把它供奉在属水之处!”
这话说出,兄弟二人几乎哭笑不得——这旱地千里,连河床都冒烟了,那还有属水的地方。
年嘉禾望向缩着头的弟弟,心中挣扎了半晌,艰难地说:”我……我家缸里还有些水。”
”好,好!
放在水缸中最好!”
孟秀才连连点头。
说干就干,三人把太岁旁边的土刨开,把它小心翼翼地抬起,那太岁外面的土灼热烫手,它本身却如玉一般冰凉润滑,触感也不坚硬,有如湿滑的菌蕈。
且凑近之后,年嘉禾才发现,那只”眼睛”,其实只是它身上那些褐色纹理汇集而成的一个图案。
这让他大松一口气。
腹中空空的三人前簇后拥、气喘吁吁,废了老大劲,才将这太岁爷抬回年嘉禾家中,小心翼翼置入水缸。
孟秀才对着水缸拜了三拜,口中叽里呱啦地念念有词,不知诵的哪家经文,又拜了三拜后,转身说要回去仔细观星卜卦,求个化凶为吉的方法,便匆匆走了。
年嘉禾回头看了看,丰登没走,正呆望着缸里的太岁。”
丰登,咋了?”
丰登响亮地咽了口口水。”
哥,这怎么看,也……也像是坨肉啊……””你又想犯浑是不是?
滚蛋!”
丰登恨恨瞪他一眼,转身走了。
两人的关系自从拆家过以后始终未改善——丰登一直不承认有偷东西。
年嘉禾在屋内来回踱了几步,只觉得心里的石头完全没落地,身上愈发地不熨帖。
那水缸像是没来由般在他视野中不停扫过,怎么躲也躲不掉,即使背过身,也仿佛就在余光处隐现。
忐忑了半天,他头晕眼花,胃一阵阵地紧缩。
上次吃东西已经不知道是几天前了。
他从床底摸出米瓮,伸手往底里抖抖索索地摸索,只抠出几粒麦壳。
但幸运的是,在床脚旁找到了半截霉烂的白薯。
他也顾不上霉,狼吞虎咽,把那半截红薯吞下肚,眯着眼躺在床上,这才慢慢缓过气来。
——今天也挺过去了。
就在这时,一阵水声清晰地传入耳朵。
年嘉禾从床上蹦起,抱住米瓮死死盯向水缸。
他绝对没听错。
是水被搅动的声音。
有东西刚才在那缸里动了。
水缸静静屹立在阴影里,看不出异样,从他所在的位置,也看不到缸内状况。
他却能清晰感觉到从缸中隐约释放出的阵阵凉意。
他甚至能听到轻微的摩擦声——仿佛有水蛇一般的物体,正用鳞片贴着缸的内壁缓缓游动。
他不敢再闭眼,就那样抱着米瓮,死盯着水缸警戒。
一直熬到后半夜,才终于抵不过困意,眼前一黑,昏睡了过去。
也没睡多久,就被哐哐的敲门声吵醒,他往屋外看了眼,天才蒙蒙亮。
打开门一看,是抱着野菜的丰登。”
哥,来……嘿,我挖到了些荠菜。”
丰登脸上的笑在尚未消退的夜色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。
年嘉禾看向弟弟怀里绿油油的菜,不由得咽了咽口水。
两人就地起火,用瓢里剩下的一点水和着野菜下锅,煎熟后揉成丸子,囫囵吞枣地分食光了。
剩下的那点菜汤也一人一口喝得精光,那绿不拉几的菜汤又苦又涩,喝下去后肚子里翻江倒海,嘴巴像鱼吐泡一样不停地吐酸水,但无论如何,这感觉总比挨饿要好得多。
丰登一边打嗝,一边用眼珠子不停地往水缸那边晃。”
哥,那肉……””那不是肉。”
年嘉禾强硬地打断。
他知道丰登在想什么。
他何尝不是。
没过多久,又传来敲门声,他把门扒开条缝一看,是孟秀才。
孟秀才像条猫一样从门缝间哧溜挤了进来,进来以后就满院子来回走,目光没个焦点地左右瞅,活像真的丢了老鼠。”
秀才,咋的?”
年嘉禾提心吊胆地问。”
不对,不对呀……””啥不对?”
”对不上,年份对不上啊……””啥年份?
你说清楚点!
别转了!”
孟秀才停下脚步,怔了一会儿,嚅嗫着说:”这、这今年是丁丑牛年,天上的星君,应该在强圉位,而这地上的太岁爷则在丑位,也就是东北方向,不该在咱这儿……不该出现在咱这儿啊!”
旁边的丰登闻言,倏地一下就站了起来。”
你说的这嘛意思?
是说,这东西不是太岁爷?”
”这、这也不应该啊……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说,这太岁的样子是”状如肉,赤者如珊瑚,白者如脂肪”,那山海经里也有写——””谁他妈管你书上怎么写!”
丰登一溜烟冲进屋。”
我就说,那不就是坨肉嘛!
恁娘的,咱三个饿汉,被一坨肉给吓到了!”
他边骂边在屋里左找右找,孟秀才见了,大概是意识到他想干嘛,也连忙往屋里走,年嘉禾愣了两秒,心里忽地念头一通,冲上去拽住孟秀才。”
你、你们……使、使不得啊嘉禾!
兴许是我没算对,又兴许是星君降错了位置呢?
你、你们要敢吃了神仙,是要遭大灾的,天大的灾难啊!”
”遭灾、遭灾!”
年嘉禾气不打一处来地骂。”
还有什么灾,能比得上咱遭的这场灾、受的这份难?
!”
”这、这……”是啊。
还有什么灾能比得上这场大旱奇荒,千里焦土?
横竖是死,做个饱肚鬼不比瘪着肚子饿死好?
他想起昨晚缸里那仿佛挑衅似的爬动声,又不知怎的想起喜穗死前的样子,胸中涌起一股杂糅了悲恨与羞愤的怒意,甩开孟秀才,一瘸一拐地走进屋,又推开丰登,从灶上的盆里抽出他找了半天的东西——许久没用的生锈菜刀。
他走到水缸边,推开虚掩的缸盖,深吸一口气,凑到缸口往里看。”
太岁”躺在缸中,用赫纹组成的巨大眼睛静静注视着他。
年嘉禾咬着牙,鼓足勇气,挥刀割下去。
等他捧着割下来的肉从缸中探出身时,额头已被冷汗浸透了。
丰登忙不迭地凑了过来,望着他手中那块拳头大小的肉。
他从”太岁”身上割肉时,那东西既没流血也没动弹,割下来的肉捧在手心,剔透晶莹,润如凝脂,让他想起了猪肉摊上油花花的大肥肉。
他不禁口舌生津,看向丰登,也在不停吞口水,就连远处的孟秀才也在偷瞄。
年嘉禾把肉细细地切下一片,凑到刚才煮野菜的余火上去炙,肉遇热并没有像猪牛羊肉一般变色焦糊、滴落油脂,反倒是赫纹褪尽,变得愈发的白皙光洁,捧在手心宛如一块美玉,也没有任何气味散发出来。
丰登迫不及待地拿起肉片,塞进口里,咀嚼了一番后,眯起眼,露出一副奇异的沉静表情。”
丰登,什么味儿?”
”……没味儿。”
”没味儿?”
”嗯,什么味儿都没有。”
”那——””好吃。”
丰登近乎沉醉地答道,一脸满足。
没味儿怎么会好吃呢?
年嘉禾带着疑问再割下一片肉来,凑到火炭上炙了炙之后,小心翼翼放进嘴中,咀嚼了几口。
他立即明白为何丰登会露出那种近乎沉醉的表情了。
这肉虽然没有任何味道,口感却异乎寻常的丰腴肥美,小小一片肉充盈了整个口腔,如同在嚼满满一大口白米饭——不对,简直比吃白米白面的感觉还要足实。
他小心翼翼吞咽下去,几乎能清晰感觉到那肉顺着喉咙,畅通无阻地落进了肚里。
吃了大半年野菜、糠皮、树根、虫子的胃激动地收缩着,把幸福的颤悸一阵阵传遍全身。
年嘉禾摸摸肚子,他甚至能感觉到那片肉就躺在肚子里,正不断地向身体倾注热量。
他看向丰登,丰登脸上也充盈着幸福的满足感,原本因饥饿而干瘪的脸颊似乎都红润了一些。
仅仅是一片肉而已。
两人又割下几片肉,放在火炭上草草炙熟后,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,几片肉下肚,二人只觉浑身燥热,这倒春寒的阴冷天气,竟热得汗流浃背。
年嘉禾脱下袄子,又割了一片肉,正欲去烤,眼角余光瞥见缩在一旁的孟秀才,孟秀才嘴里一边叨咕着造孽、遭灾之类的词,一边用金鱼眼朝他手里的肉闪闪烁烁地瞅。”
来,秀才,你也吃一点。”
孟秀才如遭电击般抖了抖,起身就往外走:”我、我不吃!”
年嘉禾朝丰登点点头,丰登会意地站起身,拦住孟秀才。”
不吃你就别走。”
两人都清楚,孟秀才就这样跑掉的话,指不定会把这太岁肉的消息传到哪里去,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把秘密和着肉一起吞下肚。
他举着肉,凑到孟秀才面前,孟秀才被丰登挟持着,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左右躲闪,喉结却在蠕动着响亮地吞咽,嘴角也渗出了亮晶晶的口水,年嘉禾不禁哂笑,把那片肉硬抵着他牙齿,塞进了他嘴里。
孟秀才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咀嚼了两下,把肉咽下肚。
很快,他也两眼放光,脸上露出充盈着满足感的幸福表情。”
这、这真乃玉馔仙馐也!”
”放什么酸屁!
说好吃就行了。”
拳头大小的肉,不到 5 分钟即被分食完毕,年嘉禾在心里数了数,他吃了 3 片,丰登吃了 5 片,而孟秀才足足吃了 8 片。
常理来说,这么小一块肉,三个饿了大半年的人分食,怎么着也不可能吃饱才对,但三人都捂着肚子,只觉得撑肠拄腹,连一粒米都再也吃不下。
他们席地而坐,抬头仰望灰蒙蒙的天空,谁也没有言语。
年嘉禾凝望着天上的太阳,他发现那太阳没有一丝温度,也不刺眼,看着黄澄澄、病恹恹的,同时肿胀得吓人,几乎盘踞了半个天空。
身上也没多少干净处,布满了菌丝一样的黑魆云气,在身体里搅拌扭动着,像是被什么祟物寄生了一样。
他看着看着,愈发觉得,那太阳马上就要被身上的菌丝给撕开了,里面的那些邪祟物即将混着漫天黄汤,无穷无尽地从天空倾泼下来。
他猛一抽搐,从幻觉中惊醒。
抬头看了看太阳,炎热又刺眼。
孟秀才颤颤巍巍站了起来,作势要走,年嘉禾见状连忙喊道:”秀才,你可别——””不说、不说……”孟秀才连连摇头。”
这等亵渎神灵的事,我哪有脸说!
就你知我知……天知地知。”
说完他低着头走出了院门,丰登也站起身。”
哥,你可要把那东西看好啊,够咱吃老久了。”
”不用你说。”
丰登一步三回头,恋恋不舍地离开了,年嘉禾呆坐在院内望了一会儿天空后,走回房,盯着角落的水缸想了想,把双手放在缸沿,用力往里推。
几十斤的缸竟让他一点点推动,被慢慢推进了阴影深处。
年嘉禾近乎有些悚栗地看着自己双手。
几个时辰前,他还是个被太阳一晒就仿佛能化掉的半死饿汉。
他捡起缸盖,盖上之前朝缸里瞅了一眼。
被割掉一角的”太岁”依然静静躺在水中,一动不动。
那只眼睛也依然气定神闲地凝视着他。
当晚,他睡得并不踏实,那眼睛在光怪陆离的梦境反复出现,一会儿揉在泥浆般的烂肉里,四处漫流,一会儿又嵌在血红肉瘤子中,不断颤动。
无数呆板愚痴的糜烂人脸攀附在墙壁上、房梁上。
他惊恐尖叫、失措地奔逃,出了满身的汗,再次在天蒙蒙亮时就惊醒了。
他抓起放在床头的水瓢,咕咚咕咚地灌,快喝完时,才模模糊糊感觉不对。
堂屋那边传来声音。
窸窸窣窣,像是有人在走动。”
……丰登!”
他鼓足勇气喊了一声,没有回应。
他慢慢起身,抓起一根破草叉,冲进堂屋。
堂屋里的人转过身看向他,年嘉禾手猛地一抖,草叉掉落在地。”
……喜穗?”
3喜穗是 10 年前逃难时经过年家村的。
年嘉禾对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记忆犹新。
那时她混在长长的逃难队伍里,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。
难民们被官差们领着,准备去县城统一安置。
年嘉禾趁其中一个官差不注意,用力把喜穗从队伍里拉出来,藏进了屋里。
事后证明,他的判断是正确的——县里的难民营不久就瘟疫横行,死掉的人堆得比城墙还高。
喜穗就这样在他家住了下来。
她家为躲避粤匪(即太平天国),举家北上逃难,家人早已在途中四散分离,举目无亲,两人就这样搭伙过起了日子。
她是个沉默寡言、勤劳能干的女人,喜穗并不是她真名,那是年嘉禾的父母准备留给他妹妹用的,但两老早早离世,这名他就挪给了她用。
两人没成过亲,也没要孩子。
年嘉禾一直觉得自己从未真正理解过这个每日同床共枕的女人,不知道她为何爱盯着榆树发笑,也不知道她每晚为谁偷偷抹泪。
这份隔阂感一直持续到她死掉。
没错。
喜穗已经死了。
他亲手埋的。
年嘉禾看着眼前的喜穗,下意识倒退两步,喜穗见状,向前迈了一步。”
嘉禾,你怎么了?”
”你、你……””我怎么了?”
”你是谁!
你咋会在这?”
”喜穗”偏着头笑了,脸上露出他再熟悉不过的两个酒窝。”
我是喜穗,是你媳妇啊,我不在自己家,还能在哪?”
”你……你少跟我撇逼,你已经死了,我亲手埋的你!”
”你看我像死了吗,嘉禾?”
喜穗平静地说,微笑着凝视他。”
来,你仔细瞧瞧,仔细看,我是不是鬼,是不是妖怪。”
”……”年嘉禾看着眼前活灵活现的女人,有些懵了。
他确实记得喜穗已经死了——是因为没东西吃活活饿死的,这刻骨铭心的事怎么可能记错?
可眼前的喜穗又真实得让他难以否定,她身上穿的花袄子,手掌上的老茧、眉头的细微伤疤,全都一模一样。
难道真是他记错了?
这大半月,他活得仿佛无魂的活尸,倒确实有可能把什么重要的事给记错。
年嘉禾止住后退的脚步,试探着向前挪了一步,死盯着喜穗的笑脸。”
你……你饿不饿?”
要真是饿死鬼,这距离,估摸着就要扑上来咬他了。
但眼前的喜穗并没有动弹,依旧只是微笑着凝视他:”我不饿,不吃东西。”
”不行、不行!
得吃点,得吃!
别又饿出病来了!”
年嘉禾大声道。
异样的喜悦迅速充盈他身心,喜穗真的回来了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——她是真没死,还是死而复生,这大半个月她又藏在了哪。
这些问题年嘉禾根本没法去思考,脑袋已全然被纯粹的喜悦给塞满。
他转过身,大步流星地走向角落的水缸。”
你等下啊,喜穗!
我给你……给你煮肉吃!
没错,咱现在有肉吃了!”
他拿起缸盖上的刀,揭开缸盖,正欲探下身割肉,忽地整个人怔住。
太岁依旧静静躺在缸中,仿佛全然没有变化。
只不过——昨天还平静凝视着他的那只眼睛,此时已经从它身上消失了。”
咋了,嘉禾?”
背后的喜穗唤道。
年嘉禾抬起身,慢慢转过头,看向身后。
喜穗用黑黝黝的明眸平静凝视着他。
他回想起来了。
十年前,他之所以冒死把她扯进屋,就是因为这双眼睛。
那时她瘦骨嶙峋、面如枯槁,佝偻得像个老妪,唯独那双眸子,却亮得仿佛能照进他的心窝,他就是在那一瞬间,打定主意要护住这点亮。
年嘉禾慢慢盖上缸盖,艰难地挤出一丝苦笑。
他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他偏开头,不再去看那双眼睛。”
……你走吧,你别呆在这。”
”走?
你要我走去哪儿?”
”马上就要来人了,他俩要看见你,就——””没事。”
喜穗低声说。”
他俩看不见我的。”
没过多久,外边传来敲门声,年嘉禾过去窥看,是丰登和孟秀才。
两人站在门边,向四周警戒地观望。
年嘉禾打开门,两人立即挤了进来,进门后就直奔水缸而去。”
哥,快点快点,我饿了!”
”你就知道饿!
谁不饿?”
年嘉禾骂了一句,紧张地向屋内看,喜穗的身影已经不见了,不知是躲起来还是消失了。
丰登找到了刀,揭开缸盖便探下身去割肉,过了一会儿,缸里瓮声瓮气传来一句:”呀,怪了!”
”咋、咋了?”
年嘉禾以为丰登也发现那只眼睛不见了,但丰登接下来的话让他不由得愣住。”
这肉咋长回去了?”
”啥?”
他疑惑地走到缸边,一旁的孟秀才也探过头,三人一齐望向水中的太岁。
丰登拍了拍太岁的一角。”
哥,你昨天割的不就是这里吗?
你还记不记得?
当时割了拳头那么大一块下来,可你看,现在竟然没痕迹了!”
”这——”年嘉禾心里一惊。
的确,眼前的太岁依然是个浑圆无缺的磨盘状,昨天割肉时的那个口子完全不见了。”
是了、是了!”
这时孟秀才忽然大喊,把二人吓了一跳。
他把头从缸里收回,一屁股坐在地上,露出追悔莫及的表情。”
啊啊啊,是了啊!”
”秀才,什么是了?”
”我昨日就想说的呀!
你俩却硬生生打断了我!
这割取又复生的神奇,便正是太岁爷的象征,山海经里就有记载!
说它『食之无尽,寻复更生如故』,又说它『奇在不尽,食人薄味』,啊啊,这就是太岁、就是太岁呀!
你们俩害死我也、害死我也!”
他说罢,就在地上捶胸顿足,嚎啕大哭起来,丰登看得烦躁,一脚蹬在他身上。”
是太岁又咋样!
我倒看它能给我降个什么天灾下来!
你要不敢吃,自己回去啃树皮去,别在这哭丧!”
孟秀才在地上打了个滚,爬起身,擦了擦长衫后,倒也不哭了。”
我吃、我吃!
我为甚不吃?
反正已经被你两给拖下水,横竖是要死了,好歹做个饱死的!”
年嘉禾抬起手,拦住正欲割肉的弟弟与孟秀才。
他偏身踟蹰许久,看向面露疑惑的二人,问道:”你俩昨天吃了这肉后,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……怪事?”
”怪事?”
”就是……有啥变化没?”
丰登和孟秀才对视一眼,同时摇头。”
真没变化?
啥都没?”
丰登想了想,说道:”就是……有劲儿了,走路不打飘了。”
”那是因为吃饱了,我不是问这个变化,秀才,你呢?”
”我……我眼力变好了。”
”眼力?”
孟秀才点点头。”
本来我这双老眼都快要瞎了的,是卦盘也看不清了,星象也看不准了。
可昨儿个吃了太岁爷的肉之后……挺邪门,眼睛看得越来越清晰,到了后半夜去看星象,这二十八宿是看得一清二楚,年轻时都没这么清楚过。
我现在啊,往远处看,少说能看个五七里路。”
”……”年嘉禾看了看孟秀才,他那两只鼓凸的鱼泡眼,确实比昨天看起来明亮不少。”
你……看到什么多余的东西没?”
”啥意思?”
”就是……不该看到的东西。”
孟秀才连连摇头,反问道:”怎的,你见到啥东西了?”
”没、没有,没啥东西。”
他这才放下手,让孟秀才和丰登探进缸里割肉。
二人割下碗那么一大块肉,你争我抢地捧到院里,开始生火炙熟,年嘉禾站在一旁怔愣地看着,没有走过去。
丰登割下一片炙熟的肉,转身看向他。”
哥,你不来吃?”
”……我不吃,”他摇摇头,”你们吃。”
丰登也懒得多说,转身把肉塞进嘴里。”
行呗,反正肉放在你这,你想啥时吃就能啥时吃。”
碗大的一块肉很快被分食干净,丰登与孟秀才的脸上再次露出那份幸福的满足感,躺在院里,迷离恍惚地仰望天空。”
这肉吃了又长,长了又能吃,那咱们是不是可以一直吃、一直长,永远都吃不完啊?”
丰登声音飘忽地说。”
若……若古书中所说属实,那的确就……就能一直吃。
本草经中还说了,这太岁肉益精气、增智慧,久服能长生不老。”
”长生不老?”
丰登鲤鱼打挺坐起,”那岂不是美极了!
我就想长生不老啊!
我说你这假秀才,你既然知道这东西这么好,却假迷三道地唬我们说什么遭灾遭灾,那是打的什么算盘?
你想独吞?”
孟秀才闷哼一声,翻了个身。”
你这辈子,见到过长生不老的人没?”
”啥?”
”没见过是吧?
就连武当的张真人,也不过活了百二十岁。
这太岁肉真要有说那么好,按理说,世上应该充满了长生不老的人才对,对不对?”
”这……”孟秀才又翻了个身。”
这灾啊,迟早是会降下来的,咱谁都逃不掉!
我清楚得很,我妈跟我说过,我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,那天上的星宿们,都……都在天上和我说话呢,等我回去再看一遍星象,再看一遍……”后面的嘟囔变得模糊不清了。
丰登嗤笑一声。”
还文曲星呢,一辈子没中秀才的老童生!”
他重新躺下,也开始迷迷糊糊地嘟囔起来。”
长生不老多好啊,那么多皇帝都求不到的美事。”
”我呀,我就想要长生不老……永远都不死……”二人就那样一横一竖地躺着,浑浑噩噩地胡言乱语,年嘉禾也懒得搭理他们,蹲在一旁冷眼观望。
他知道这两人的样子也绝对不正常,他们虽不像他那样看见了死人,却同样在发生着某种不知名的变化。
那”肉”肯定不对劲。
不能再吃了。
可怎么才能说服他俩不要吃呢?
他正苦恼间,忽然感觉视线边缘有什么东西一闪,急转头去看时,正好看见院墙顶上一个飞快缩回墙后的头,他怔了一瞬,心中警铃大作。”
有、有人!”
他一边大声喊,一边使劲去摇睡得晕乎乎的丰登和孟秀才。
小说:末日游戏:我在洪流中求生存
类型:小说推荐
作者:沈客
角色:陆远我叫明瑶
热门新书《末日游戏:我在洪流中求生存》是由著名网文作者“沈客”所著的小说推荐分类小说。文章简述:灶房里趴了个皮包骨头的人,那是四妹,她正趴在灶边,朝里塞枯叶、吹风,灶上的破锅里煮着一锅沸肉汤。”四、四妹……”四妹转过头,一脸恐惧地朝他拼命摆手。”莫喊,姨哥,莫喊,我分你,我分你一条腿。”年嘉禾咽了口酸水
评论专区
当医生开了外挂:作者把轻佻逗逼当成了轻松幽默,看多了让人恶心。
我是至尊:“ 是堆积如山的玄兽肉。一阵阵异香扑鼻。只是,这分量也太多了一些。 粗略看去,四五十斤是有的。”四五十斤就“堆积如山”,杀一头肥猪得多少山
重生之风流仕途:惊闻

第 1 节 太岁
外边突然传来一声稚嫩的凄叫,把年嘉禾猛地惊醒,还没等他起身,那惨叫声就迅速萎弱了下去。
他撑起身,爬下茅草床,杵着木棍,拖着浮肿的腿,摸到门边扒开条缝,朝外瞄了一眼,巷里没人。
不是路倒。
但不远处四妹家的院子里正传来有规律的劈砍声,过了一阵,袅袅白烟从那里升起,竟有一阵肉香味顺着冷风飘了过来。
年嘉禾肚里猛一颤,肠胃咕噜蠕动着,呕出了一小口酸水。
他只觉得本来薄似纸、透似纱,风一吹就能飘起来的身体,竟被那香味勾得稍稍有了些重量。
他推开门,一颠一瘸地走到四妹家,敲了敲门以后,便忙不迭地推开。
灶房里趴了个皮包骨头的人,那是四妹,她正趴在灶边,朝里塞枯叶、吹风,灶上的破锅里煮着一锅沸肉汤。”
四、四妹……”四妹转过头,一脸恐惧地朝他拼命摆手。”
莫喊,姨哥,莫喊,我分你,我分你一条腿。”
年嘉禾咽了口酸水。”
……你这煮的什么肉?
老鼠都没了,你煮的什么肉?”
四妹用黢黑的手抹了把脸,喜不自禁地说:”猪崽子!
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了一只猪崽子,饿得走不动了,我把它抱住了,一把就抱住了!”
年嘉禾凑近那锅沸腾着的汤,睁大眼仔细看了看,哆嗦着腿往后退一步。”
这不是猪崽子。”
”不、不是猪崽子?
怎么会呢?”
四妹呆滞地喃道。”
我抱住它了的啊,我真的抱住了,好大一只,不是猪崽子,还能是啥?”
”这是家兴。”
年嘉禾说。”
家兴?”
四妹的脸上露出茫然而迟钝的表情。”
家兴是谁?”
”是你的娃。”
”……”过了好几秒,都没有回应,年嘉禾不得不抬头看向四妹。
她仿佛生了根一般,一动不动地坐在原地,那份茫然迟钝的表情硬邦邦地凝固在她脸上。
枯叶在灶里噼啪作响,沸腾的开水溢出锅子,淌在血淋淋的灶台上,四妹依然毫无反应,仿佛变成了一尊泥塑。
年嘉禾转过身,慢慢走出四妹家。
过了几秒,他听见背后传来撕心裂肺的凄嚎。
第二天,腐臭味顺着风飘了过来,年嘉禾拄起棍走过去,推开灶房门,四妹倒在地上,没了气息。
他早已没了挖坑的气力,只得用茅草与破布给她草草盖上。
当晚,对面还是响起了凌乱沉重的脚步声,以及刻意压低的说话声。
年嘉禾知道那些人是在干什么。
他没有余力去制止。
大旱已经持续了两年多。
第一年,就几乎颗粒无收,连土豆都闷死在了地里,没能抢出来一块。
县里倒是早早发了赈灾粮,可层层克扣下来,发到手上就只剩下一小袋掺了糠和沙的麦子,还不够煮一锅粥。
靠着存粮,年家村熬过了那个严酷的冬天,只走了几个老人。
第二年开春,倒是下了几场好雨,雾凇挂满枝桠,颇具丰年瑞兆。
可惜二月之后焦旱再至,麦苗还没抽穗就死了十之八九。
火上浇油的是蝗也来了,铺天盖地刮过去,将残存的苗也吃得一干二净。
赈灾粮没了,粥厂也没人开了——别说是县里,就连直隶都已经没粮了。
从那时开始,大饥荒便真正降临了。
年嘉禾依然清楚地记得去年冬天的每个日夜——因为每天晚上,都至少会有一家传出哭声。
那就代表又死了一个。
到后来,连哭声都变得低微而压抑——怕人循着哭声,翻进屋里抢尸体。
饿啊。
饿得人根本挪不动窝,说不出话,只能平地躺着,像数数一样地进气、出气,像是给自己的命作倒数。
有力气逃难的基本都逃光了,壮实的、年轻的、有点家底的。
年嘉禾没跟着逃难,他天生跛足,知道自己逃不远。
喜穗也没逃。
无论他怎么劝、怎么骂、怎么赶,她都没逃。
她熬过了冬天,是在开春后咽气的。
她咽气的那天,正好是最后一波蝗飞走,年嘉禾从寸草不生的田里回到寂静无声的家,才发现家里的喜穗也没了。
她弥留那几天,一直在半清醒半迷糊地呢喃。”
嘉禾……去找蛇。”
”找蛇?
找蛇干什么?”
”去找蛇……蛇多的地方有泉眼……”有泉眼兴许就能打出井,打出井来就能灌田了。
喜穗至死都在惦记这个。
可她哪知道,别说蛇,就连老鼠、蚯蚓、蟑螂,都已经被吃光了。
她是闹粤匪时从南方逃难过来的,这些年跟着他,基本没过上几天饱日子。
年嘉禾一声也没敢哭。
他用草席把她包好,埋在了院前的大榆树下面。
榆树的树皮早已被扒光,但枝桠上还在倔强地发着芽,本来再熬个把月,她就能吃到她最喜欢的榆钱儿。
熬吧。
年嘉禾呆坐在门口,望着眼前的漫漫黄土。
等熬过这段旱,看老天爷能不能赏脸,下两场雨,补种点芋头、土豆下去,好歹能收点粮。
好歹能活下去。
活下去干啥呢?
年嘉禾茫然地望着荒村。
往年他是根本没时间去思考这种问题的,他要忙着打秆、松土、施肥、除虫、引水、割麦、打谷……一年到头都忙得像个陀螺,根本停不下来。
哪怕到了冬天,能歇息一下了,心里想着的也是来年啥时播种、存粮够不够吃。
光是活下来就已经足够艰苦了,根本没时间想其他的。
可到了如今,在这数着数儿进气出气的关头,年嘉禾反倒有闲暇思考了。
活着到底图个啥呢?
传宗接代?
光耀门楣?
一阵睡意袭来。
年嘉禾使劲摇摇头,用力揭开快粘住的上下眼皮,他知道要是在这会儿阖眼,很可能就永远也睁不开了。
他不知道活着到底图啥,但他本能地想活着。
远处的干涸河床里,有个缓缓蠕动的黑影,像是条快晒干的蚯蚓,年嘉禾睁大眼仔细瞅了瞅。
是丰登,他弟弟。
这种时候还能有力气在外走动的也不剩几个了,丰登便是其中之一。
丰登匍匐在地上,像蚯蚓般一寸一寸地挪着,他正在龟裂的土块里翻找虫子与树根。
他也已经瘦得跟骷髅一样了,颧骨如两座山一样暴突高耸,眼窝与面颊却如深潭般凹陷,枯皱黯淡的脸上,唯有两只眼珠子亮得吓人,泛出红光。
年嘉禾打个寒颤,他想起了昨晚的事。
偷尸抢尸早已不是新鲜事了,有更恐怖的传言说,附近山中的粤匪残党正在拦路劫杀活人。
丰登从小就是个顽劣的孩子,不干农活,也不读书。
他们原本一起住,但他手脚不干净,偷家里的东西,年嘉禾一怒之下便将他赶出了屋。
那之后他便游手好闲,东家讨一顿饭、西家讨一顿打地混世度日。
这场奇荒降临后,年嘉禾本以为他会是最先熬不住的那批人,但没曾想,丰登的身体里迸发出了一股奇异的生命力,在这干裂的大地上比谁都更努力地挣扎求生。
就像条蚯蚓一样。
——他这么努力地活着,又是图些啥?
这时,一道白光忽地从天空划过,年嘉禾抬头看时,那光已经烈烈灼目如第二个太阳。
再眨眼时,光又不见了,只在天上留下一道辣眼的白痕子,紧接着远处的山坳传来一声炸雷般巨响,把年嘉禾从门槛上猛掀倒在地。
他哆嗦着爬起身,望向巨响传来的方向,只见那边山坳深处正缓缓袅出黑烟。”
这……这咋回事?”
天上咋掉了个太阳下来?
他正欲仔细看,只见下面的丰登爬起了身,顺着河床朝黑烟飘出的山坳走去,年嘉禾瞬间激出了一背心冷汗,朝弟弟的背影用力喊:”丰登……别去!
你个寡货,别过去!”
可丰登压根听不见,丢了魂似的兀自走着,他只得竭力撑起身子,一瘸一拐地追上丰登的背影。
天上的太阳光照下来,他只觉自己纸一样的身躯被照了个透亮,脚步竟有些轻盈起来了,仿佛稍一踮脚,就能轻飘飘地飞起来一样,他就这样跟着丰登,两人一前一后,一脚深一脚浅地摸进了那山坳,踩着碎石,小心翼翼、连滚带爬地滑下斜坡,往那黑烟袅起的地方望去。
焦金流石的河床**,凹下去一个两三米宽的大坑,坑的**是一个石磨大小的土丘,土丘外围是向四周翻开的泥土,里面混合着被烧黑的杂草和枯根,散发出难闻的糊味。
丰登从泥土里拨出一截没有彻底烧焦的树根,草草擦了下以后,就塞进嘴里,混合着唾沫咀嚼吞咽了下去。”
别吃!
你个挨刀货!
有毒怎么办!”
年嘉禾有气无力地骂了两句,试探着朝焦坑**的土丘走去,坑里的土还很灼热,阵阵散发着热浪与白烟,年嘉禾只走了一步,便觉得自己鼻孔都快冒火了,没敢再靠近。
他总觉得那堆土在缓缓地颤动。
不知道是不是热浪导致的错觉。
他捡起一根枯枝,小心翼翼戳了戳,土丘猛地一个震颤,从顶端抖落了不少焦土。
这次绝对不是错觉。
他抹了抹虚汗,用力再捅过去。
大量焦土随着抖颤从”土丘”身上抖落,年嘉禾扔掉树枝,倒退着坐倒在地——他从土丘的内部,看到了一只紧盯着他的眼睛。
丰登走到他身边捡起树枝,把”土丘”上剩下的土层扫掉,随后和年嘉禾一起坐倒在地。
土丘里面是一团磨盘大小,灰白底色,遍布赫色纹理的块状物体。”
……肉?”
丰登颤声道。
那的确像是一块肉。
而他看到的眼睛,就是那坨肉上唯一的器官。
2”造孽——造孽啊!”
背后传来拉长的凄嚎。
二人转头看去,见到一名穿着褴褛长衫的黑瘦老头。
那人是村里的教书先生,孟秀才。
孟秀才其实不算真秀才,他没中过功名,一辈子都只是个老童生。
但他好歹是村里为数不多识字的人,办过几年塾,逢年过节帮人写对联、家书之类,因此村里人都愿尊称他一声秀才。
只不过他终年无法进学,落了心疾,又沉迷起黄老、命理之类偏门学问,便常有些疯癫的举止,常在口里念叨着些”天地玄黄”之类的话四处游荡,村里人都不怎么敢接近他。
他也是大荒来临后,还有力气在外走动的人之一,他仍穿着那件皱巴巴的长衫,因消瘦而暴突的双眼像金鱼一样鼓瞪着,用鸡爪手颤巍巍地指向坑中的肉块。”
造孽啊,你们俩!
你俩闯大祸啦!
你们俩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啦!”
年嘉禾闻言猛一激灵,回头看向肉块。”
秀才,你……你说这是什么?”
”太岁!
是太岁爷啊!
是神仙!
那天上的太岁星君,在黄道太虚上遨游,每至一星次,就在对应的地面上降下一尊太岁爷来。
你们两个挨刀货,刚才干了什么?
你们竟然用棍子在太岁爷头上扫土!
你们冒犯了神仙,整个村子都要跟你们一起遭灾啦!”
年嘉禾不禁心中悚然,转头看了看丰登,也面色发白。
太岁爷降灾的说法,他以前确实听长辈们说过,说有人挖出了太岁,又惧而填埋,导致兄弟妻儿数日内悉数暴毙,他一时间也没了主意,只能眼巴巴地望向孟秀才。”
秀、秀才,那……那我们该怎么办?”
孟秀才转着鼓突的金鱼眼,低头思忖了片刻。”
不管怎的,咱先得把太岁爷好好供奉起来,兴许能让它不降灾祸!
我想想……这星君五行属木,按相生之理,得把它供奉在属水之处!”
这话说出,兄弟二人几乎哭笑不得——这旱地千里,连河床都冒烟了,那还有属水的地方。
年嘉禾望向缩着头的弟弟,心中挣扎了半晌,艰难地说:”我……我家缸里还有些水。”
”好,好!
放在水缸中最好!”
孟秀才连连点头。
说干就干,三人把太岁旁边的土刨开,把它小心翼翼地抬起,那太岁外面的土灼热烫手,它本身却如玉一般冰凉润滑,触感也不坚硬,有如湿滑的菌蕈。
且凑近之后,年嘉禾才发现,那只”眼睛”,其实只是它身上那些褐色纹理汇集而成的一个图案。
这让他大松一口气。
腹中空空的三人前簇后拥、气喘吁吁,废了老大劲,才将这太岁爷抬回年嘉禾家中,小心翼翼置入水缸。
孟秀才对着水缸拜了三拜,口中叽里呱啦地念念有词,不知诵的哪家经文,又拜了三拜后,转身说要回去仔细观星卜卦,求个化凶为吉的方法,便匆匆走了。
年嘉禾回头看了看,丰登没走,正呆望着缸里的太岁。”
丰登,咋了?”
丰登响亮地咽了口口水。”
哥,这怎么看,也……也像是坨肉啊……””你又想犯浑是不是?
滚蛋!”
丰登恨恨瞪他一眼,转身走了。
两人的关系自从拆家过以后始终未改善——丰登一直不承认有偷东西。
年嘉禾在屋内来回踱了几步,只觉得心里的石头完全没落地,身上愈发地不熨帖。
那水缸像是没来由般在他视野中不停扫过,怎么躲也躲不掉,即使背过身,也仿佛就在余光处隐现。
忐忑了半天,他头晕眼花,胃一阵阵地紧缩。
上次吃东西已经不知道是几天前了。
他从床底摸出米瓮,伸手往底里抖抖索索地摸索,只抠出几粒麦壳。
但幸运的是,在床脚旁找到了半截霉烂的白薯。
他也顾不上霉,狼吞虎咽,把那半截红薯吞下肚,眯着眼躺在床上,这才慢慢缓过气来。
——今天也挺过去了。
就在这时,一阵水声清晰地传入耳朵。
年嘉禾从床上蹦起,抱住米瓮死死盯向水缸。
他绝对没听错。
是水被搅动的声音。
有东西刚才在那缸里动了。
水缸静静屹立在阴影里,看不出异样,从他所在的位置,也看不到缸内状况。
他却能清晰感觉到从缸中隐约释放出的阵阵凉意。
他甚至能听到轻微的摩擦声——仿佛有水蛇一般的物体,正用鳞片贴着缸的内壁缓缓游动。
他不敢再闭眼,就那样抱着米瓮,死盯着水缸警戒。
一直熬到后半夜,才终于抵不过困意,眼前一黑,昏睡了过去。
也没睡多久,就被哐哐的敲门声吵醒,他往屋外看了眼,天才蒙蒙亮。
打开门一看,是抱着野菜的丰登。”
哥,来……嘿,我挖到了些荠菜。”
丰登脸上的笑在尚未消退的夜色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。
年嘉禾看向弟弟怀里绿油油的菜,不由得咽了咽口水。
两人就地起火,用瓢里剩下的一点水和着野菜下锅,煎熟后揉成丸子,囫囵吞枣地分食光了。
剩下的那点菜汤也一人一口喝得精光,那绿不拉几的菜汤又苦又涩,喝下去后肚子里翻江倒海,嘴巴像鱼吐泡一样不停地吐酸水,但无论如何,这感觉总比挨饿要好得多。
丰登一边打嗝,一边用眼珠子不停地往水缸那边晃。”
哥,那肉……””那不是肉。”
年嘉禾强硬地打断。
他知道丰登在想什么。
他何尝不是。
没过多久,又传来敲门声,他把门扒开条缝一看,是孟秀才。
孟秀才像条猫一样从门缝间哧溜挤了进来,进来以后就满院子来回走,目光没个焦点地左右瞅,活像真的丢了老鼠。”
秀才,咋的?”
年嘉禾提心吊胆地问。”
不对,不对呀……””啥不对?”
”对不上,年份对不上啊……””啥年份?
你说清楚点!
别转了!”
孟秀才停下脚步,怔了一会儿,嚅嗫着说:”这、这今年是丁丑牛年,天上的星君,应该在强圉位,而这地上的太岁爷则在丑位,也就是东北方向,不该在咱这儿……不该出现在咱这儿啊!”
旁边的丰登闻言,倏地一下就站了起来。”
你说的这嘛意思?
是说,这东西不是太岁爷?”
”这、这也不应该啊……《本草纲目》中就说,这太岁的样子是”状如肉,赤者如珊瑚,白者如脂肪”,那山海经里也有写——””谁他妈管你书上怎么写!”
丰登一溜烟冲进屋。”
我就说,那不就是坨肉嘛!
恁娘的,咱三个饿汉,被一坨肉给吓到了!”
他边骂边在屋里左找右找,孟秀才见了,大概是意识到他想干嘛,也连忙往屋里走,年嘉禾愣了两秒,心里忽地念头一通,冲上去拽住孟秀才。”
你、你们……使、使不得啊嘉禾!
兴许是我没算对,又兴许是星君降错了位置呢?
你、你们要敢吃了神仙,是要遭大灾的,天大的灾难啊!”
”遭灾、遭灾!”
年嘉禾气不打一处来地骂。”
还有什么灾,能比得上咱遭的这场灾、受的这份难?
!”
”这、这……”是啊。
还有什么灾能比得上这场大旱奇荒,千里焦土?
横竖是死,做个饱肚鬼不比瘪着肚子饿死好?
他想起昨晚缸里那仿佛挑衅似的爬动声,又不知怎的想起喜穗死前的样子,胸中涌起一股杂糅了悲恨与羞愤的怒意,甩开孟秀才,一瘸一拐地走进屋,又推开丰登,从灶上的盆里抽出他找了半天的东西——许久没用的生锈菜刀。
他走到水缸边,推开虚掩的缸盖,深吸一口气,凑到缸口往里看。”
太岁”躺在缸中,用赫纹组成的巨大眼睛静静注视着他。
年嘉禾咬着牙,鼓足勇气,挥刀割下去。
等他捧着割下来的肉从缸中探出身时,额头已被冷汗浸透了。
丰登忙不迭地凑了过来,望着他手中那块拳头大小的肉。
他从”太岁”身上割肉时,那东西既没流血也没动弹,割下来的肉捧在手心,剔透晶莹,润如凝脂,让他想起了猪肉摊上油花花的大肥肉。
他不禁口舌生津,看向丰登,也在不停吞口水,就连远处的孟秀才也在偷瞄。
年嘉禾把肉细细地切下一片,凑到刚才煮野菜的余火上去炙,肉遇热并没有像猪牛羊肉一般变色焦糊、滴落油脂,反倒是赫纹褪尽,变得愈发的白皙光洁,捧在手心宛如一块美玉,也没有任何气味散发出来。
丰登迫不及待地拿起肉片,塞进口里,咀嚼了一番后,眯起眼,露出一副奇异的沉静表情。”
丰登,什么味儿?”
”……没味儿。”
”没味儿?”
”嗯,什么味儿都没有。”
”那——””好吃。”
丰登近乎沉醉地答道,一脸满足。
没味儿怎么会好吃呢?
年嘉禾带着疑问再割下一片肉来,凑到火炭上炙了炙之后,小心翼翼放进嘴中,咀嚼了几口。
他立即明白为何丰登会露出那种近乎沉醉的表情了。
这肉虽然没有任何味道,口感却异乎寻常的丰腴肥美,小小一片肉充盈了整个口腔,如同在嚼满满一大口白米饭——不对,简直比吃白米白面的感觉还要足实。
他小心翼翼吞咽下去,几乎能清晰感觉到那肉顺着喉咙,畅通无阻地落进了肚里。
吃了大半年野菜、糠皮、树根、虫子的胃激动地收缩着,把幸福的颤悸一阵阵传遍全身。
年嘉禾摸摸肚子,他甚至能感觉到那片肉就躺在肚子里,正不断地向身体倾注热量。
他看向丰登,丰登脸上也充盈着幸福的满足感,原本因饥饿而干瘪的脸颊似乎都红润了一些。
仅仅是一片肉而已。
两人又割下几片肉,放在火炭上草草炙熟后,迫不及待地送进嘴里,几片肉下肚,二人只觉浑身燥热,这倒春寒的阴冷天气,竟热得汗流浃背。
年嘉禾脱下袄子,又割了一片肉,正欲去烤,眼角余光瞥见缩在一旁的孟秀才,孟秀才嘴里一边叨咕着造孽、遭灾之类的词,一边用金鱼眼朝他手里的肉闪闪烁烁地瞅。”
来,秀才,你也吃一点。”
孟秀才如遭电击般抖了抖,起身就往外走:”我、我不吃!”
年嘉禾朝丰登点点头,丰登会意地站起身,拦住孟秀才。”
不吃你就别走。”
两人都清楚,孟秀才就这样跑掉的话,指不定会把这太岁肉的消息传到哪里去,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让他把秘密和着肉一起吞下肚。
他举着肉,凑到孟秀才面前,孟秀才被丰登挟持着,摆出一副宁死不屈的架势左右躲闪,喉结却在蠕动着响亮地吞咽,嘴角也渗出了亮晶晶的口水,年嘉禾不禁哂笑,把那片肉硬抵着他牙齿,塞进了他嘴里。
孟秀才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咀嚼了两下,把肉咽下肚。
很快,他也两眼放光,脸上露出充盈着满足感的幸福表情。”
这、这真乃玉馔仙馐也!”
”放什么酸屁!
说好吃就行了。”
拳头大小的肉,不到 5 分钟即被分食完毕,年嘉禾在心里数了数,他吃了 3 片,丰登吃了 5 片,而孟秀才足足吃了 8 片。
常理来说,这么小一块肉,三个饿了大半年的人分食,怎么着也不可能吃饱才对,但三人都捂着肚子,只觉得撑肠拄腹,连一粒米都再也吃不下。
他们席地而坐,抬头仰望灰蒙蒙的天空,谁也没有言语。
年嘉禾凝望着天上的太阳,他发现那太阳没有一丝温度,也不刺眼,看着黄澄澄、病恹恹的,同时肿胀得吓人,几乎盘踞了半个天空。
身上也没多少干净处,布满了菌丝一样的黑魆云气,在身体里搅拌扭动着,像是被什么祟物寄生了一样。
他看着看着,愈发觉得,那太阳马上就要被身上的菌丝给撕开了,里面的那些邪祟物即将混着漫天黄汤,无穷无尽地从天空倾泼下来。
他猛一抽搐,从幻觉中惊醒。
抬头看了看太阳,炎热又刺眼。
孟秀才颤颤巍巍站了起来,作势要走,年嘉禾见状连忙喊道:”秀才,你可别——””不说、不说……”孟秀才连连摇头。”
这等亵渎神灵的事,我哪有脸说!
就你知我知……天知地知。”
说完他低着头走出了院门,丰登也站起身。”
哥,你可要把那东西看好啊,够咱吃老久了。”
”不用你说。”
丰登一步三回头,恋恋不舍地离开了,年嘉禾呆坐在院内望了一会儿天空后,走回房,盯着角落的水缸想了想,把双手放在缸沿,用力往里推。
几十斤的缸竟让他一点点推动,被慢慢推进了阴影深处。
年嘉禾近乎有些悚栗地看着自己双手。
几个时辰前,他还是个被太阳一晒就仿佛能化掉的半死饿汉。
他捡起缸盖,盖上之前朝缸里瞅了一眼。
被割掉一角的”太岁”依然静静躺在水中,一动不动。
那只眼睛也依然气定神闲地凝视着他。
当晚,他睡得并不踏实,那眼睛在光怪陆离的梦境反复出现,一会儿揉在泥浆般的烂肉里,四处漫流,一会儿又嵌在血红肉瘤子中,不断颤动。
无数呆板愚痴的糜烂人脸攀附在墙壁上、房梁上。
他惊恐尖叫、失措地奔逃,出了满身的汗,再次在天蒙蒙亮时就惊醒了。
他抓起放在床头的水瓢,咕咚咕咚地灌,快喝完时,才模模糊糊感觉不对。
堂屋那边传来声音。
窸窸窣窣,像是有人在走动。”
……丰登!”
他鼓足勇气喊了一声,没有回应。
他慢慢起身,抓起一根破草叉,冲进堂屋。
堂屋里的人转过身看向他,年嘉禾手猛地一抖,草叉掉落在地。”
……喜穗?”
3喜穗是 10 年前逃难时经过年家村的。
年嘉禾对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情景还记忆犹新。
那时她混在长长的逃难队伍里,蓬头垢面、衣衫褴褛。
难民们被官差们领着,准备去县城统一安置。
年嘉禾趁其中一个官差不注意,用力把喜穗从队伍里拉出来,藏进了屋里。
事后证明,他的判断是正确的——县里的难民营不久就瘟疫横行,死掉的人堆得比城墙还高。
喜穗就这样在他家住了下来。
她家为躲避粤匪(即太平天国),举家北上逃难,家人早已在途中四散分离,举目无亲,两人就这样搭伙过起了日子。
她是个沉默寡言、勤劳能干的女人,喜穗并不是她真名,那是年嘉禾的父母准备留给他妹妹用的,但两老早早离世,这名他就挪给了她用。
两人没成过亲,也没要孩子。
年嘉禾一直觉得自己从未真正理解过这个每日同床共枕的女人,不知道她为何爱盯着榆树发笑,也不知道她每晚为谁偷偷抹泪。
这份隔阂感一直持续到她死掉。
没错。
喜穗已经死了。
他亲手埋的。
年嘉禾看着眼前的喜穗,下意识倒退两步,喜穗见状,向前迈了一步。”
嘉禾,你怎么了?”
”你、你……””我怎么了?”
”你是谁!
你咋会在这?”
”喜穗”偏着头笑了,脸上露出他再熟悉不过的两个酒窝。”
我是喜穗,是你媳妇啊,我不在自己家,还能在哪?”
”你……你少跟我撇逼,你已经死了,我亲手埋的你!”
”你看我像死了吗,嘉禾?”
喜穗平静地说,微笑着凝视他。”
来,你仔细瞧瞧,仔细看,我是不是鬼,是不是妖怪。”
”……”年嘉禾看着眼前活灵活现的女人,有些懵了。
他确实记得喜穗已经死了——是因为没东西吃活活饿死的,这刻骨铭心的事怎么可能记错?
可眼前的喜穗又真实得让他难以否定,她身上穿的花袄子,手掌上的老茧、眉头的细微伤疤,全都一模一样。
难道真是他记错了?
这大半月,他活得仿佛无魂的活尸,倒确实有可能把什么重要的事给记错。
年嘉禾止住后退的脚步,试探着向前挪了一步,死盯着喜穗的笑脸。”
你……你饿不饿?”
要真是饿死鬼,这距离,估摸着就要扑上来咬他了。
但眼前的喜穗并没有动弹,依旧只是微笑着凝视他:”我不饿,不吃东西。”
”不行、不行!
得吃点,得吃!
别又饿出病来了!”
年嘉禾大声道。
异样的喜悦迅速充盈他身心,喜穗真的回来了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——她是真没死,还是死而复生,这大半个月她又藏在了哪。
这些问题年嘉禾根本没法去思考,脑袋已全然被纯粹的喜悦给塞满。
他转过身,大步流星地走向角落的水缸。”
你等下啊,喜穗!
我给你……给你煮肉吃!
没错,咱现在有肉吃了!”
他拿起缸盖上的刀,揭开缸盖,正欲探下身割肉,忽地整个人怔住。
太岁依旧静静躺在缸中,仿佛全然没有变化。
只不过——昨天还平静凝视着他的那只眼睛,此时已经从它身上消失了。”
咋了,嘉禾?”
背后的喜穗唤道。
年嘉禾抬起身,慢慢转过头,看向身后。
喜穗用黑黝黝的明眸平静凝视着他。
他回想起来了。
十年前,他之所以冒死把她扯进屋,就是因为这双眼睛。
那时她瘦骨嶙峋、面如枯槁,佝偻得像个老妪,唯独那双眸子,却亮得仿佛能照进他的心窝,他就是在那一瞬间,打定主意要护住这点亮。
年嘉禾慢慢盖上缸盖,艰难地挤出一丝苦笑。
他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
他偏开头,不再去看那双眼睛。”
……你走吧,你别呆在这。”
”走?
你要我走去哪儿?”
”马上就要来人了,他俩要看见你,就——””没事。”
喜穗低声说。”
他俩看不见我的。”
没过多久,外边传来敲门声,年嘉禾过去窥看,是丰登和孟秀才。
两人站在门边,向四周警戒地观望。
年嘉禾打开门,两人立即挤了进来,进门后就直奔水缸而去。”
哥,快点快点,我饿了!”
”你就知道饿!
谁不饿?”
年嘉禾骂了一句,紧张地向屋内看,喜穗的身影已经不见了,不知是躲起来还是消失了。
丰登找到了刀,揭开缸盖便探下身去割肉,过了一会儿,缸里瓮声瓮气传来一句:”呀,怪了!”
”咋、咋了?”
年嘉禾以为丰登也发现那只眼睛不见了,但丰登接下来的话让他不由得愣住。”
这肉咋长回去了?”
”啥?”
他疑惑地走到缸边,一旁的孟秀才也探过头,三人一齐望向水中的太岁。
丰登拍了拍太岁的一角。”
哥,你昨天割的不就是这里吗?
你还记不记得?
当时割了拳头那么大一块下来,可你看,现在竟然没痕迹了!”
”这——”年嘉禾心里一惊。
的确,眼前的太岁依然是个浑圆无缺的磨盘状,昨天割肉时的那个口子完全不见了。”
是了、是了!”
这时孟秀才忽然大喊,把二人吓了一跳。
他把头从缸里收回,一屁股坐在地上,露出追悔莫及的表情。”
啊啊啊,是了啊!”
”秀才,什么是了?”
”我昨日就想说的呀!
你俩却硬生生打断了我!
这割取又复生的神奇,便正是太岁爷的象征,山海经里就有记载!
说它『食之无尽,寻复更生如故』,又说它『奇在不尽,食人薄味』,啊啊,这就是太岁、就是太岁呀!
你们俩害死我也、害死我也!”
他说罢,就在地上捶胸顿足,嚎啕大哭起来,丰登看得烦躁,一脚蹬在他身上。”
是太岁又咋样!
我倒看它能给我降个什么天灾下来!
你要不敢吃,自己回去啃树皮去,别在这哭丧!”
孟秀才在地上打了个滚,爬起身,擦了擦长衫后,倒也不哭了。”
我吃、我吃!
我为甚不吃?
反正已经被你两给拖下水,横竖是要死了,好歹做个饱死的!”
年嘉禾抬起手,拦住正欲割肉的弟弟与孟秀才。
他偏身踟蹰许久,看向面露疑惑的二人,问道:”你俩昨天吃了这肉后,身上有没有发生什么……怪事?”
”怪事?”
”就是……有啥变化没?”
丰登和孟秀才对视一眼,同时摇头。”
真没变化?
啥都没?”
丰登想了想,说道:”就是……有劲儿了,走路不打飘了。”
”那是因为吃饱了,我不是问这个变化,秀才,你呢?”
”我……我眼力变好了。”
”眼力?”
孟秀才点点头。”
本来我这双老眼都快要瞎了的,是卦盘也看不清了,星象也看不准了。
可昨儿个吃了太岁爷的肉之后……挺邪门,眼睛看得越来越清晰,到了后半夜去看星象,这二十八宿是看得一清二楚,年轻时都没这么清楚过。
我现在啊,往远处看,少说能看个五七里路。”
”……”年嘉禾看了看孟秀才,他那两只鼓凸的鱼泡眼,确实比昨天看起来明亮不少。”
你……看到什么多余的东西没?”
”啥意思?”
”就是……不该看到的东西。”
孟秀才连连摇头,反问道:”怎的,你见到啥东西了?”
”没、没有,没啥东西。”
他这才放下手,让孟秀才和丰登探进缸里割肉。
二人割下碗那么一大块肉,你争我抢地捧到院里,开始生火炙熟,年嘉禾站在一旁怔愣地看着,没有走过去。
丰登割下一片炙熟的肉,转身看向他。”
哥,你不来吃?”
”……我不吃,”他摇摇头,”你们吃。”
丰登也懒得多说,转身把肉塞进嘴里。”
行呗,反正肉放在你这,你想啥时吃就能啥时吃。”
碗大的一块肉很快被分食干净,丰登与孟秀才的脸上再次露出那份幸福的满足感,躺在院里,迷离恍惚地仰望天空。”
这肉吃了又长,长了又能吃,那咱们是不是可以一直吃、一直长,永远都吃不完啊?”
丰登声音飘忽地说。”
若……若古书中所说属实,那的确就……就能一直吃。
本草经中还说了,这太岁肉益精气、增智慧,久服能长生不老。”
”长生不老?”
丰登鲤鱼打挺坐起,”那岂不是美极了!
我就想长生不老啊!
我说你这假秀才,你既然知道这东西这么好,却假迷三道地唬我们说什么遭灾遭灾,那是打的什么算盘?
你想独吞?”
孟秀才闷哼一声,翻了个身。”
你这辈子,见到过长生不老的人没?”
”啥?”
”没见过是吧?
就连武当的张真人,也不过活了百二十岁。
这太岁肉真要有说那么好,按理说,世上应该充满了长生不老的人才对,对不对?”
”这……”孟秀才又翻了个身。”
这灾啊,迟早是会降下来的,咱谁都逃不掉!
我清楚得很,我妈跟我说过,我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,那天上的星宿们,都……都在天上和我说话呢,等我回去再看一遍星象,再看一遍……”后面的嘟囔变得模糊不清了。
丰登嗤笑一声。”
还文曲星呢,一辈子没中秀才的老童生!”
他重新躺下,也开始迷迷糊糊地嘟囔起来。”
长生不老多好啊,那么多皇帝都求不到的美事。”
”我呀,我就想要长生不老……永远都不死……”二人就那样一横一竖地躺着,浑浑噩噩地胡言乱语,年嘉禾也懒得搭理他们,蹲在一旁冷眼观望。
他知道这两人的样子也绝对不正常,他们虽不像他那样看见了死人,却同样在发生着某种不知名的变化。
那”肉”肯定不对劲。
不能再吃了。
可怎么才能说服他俩不要吃呢?
他正苦恼间,忽然感觉视线边缘有什么东西一闪,急转头去看时,正好看见院墙顶上一个飞快缩回墙后的头,他怔了一瞬,心中警铃大作。”
有、有人!”
他一边大声喊,一边使劲去摇睡得晕乎乎的丰登和孟秀才。
千亿体育_千亿体育官网_千亿APP_千亿体育平台(www.qytygw.com)会员自助返水最高28888元,千亿宝贝等你撩
球盟会-球盟会官网-球盟会体育是亚洲老牌娱乐平台(www.qmhtyw.com)最好足球投注平台,开户送88元,美女宝贝空降!
龙8国际-龙8国际官网-龙八国际娱乐官网-龙八国际娱乐下载(www.l8gjw.com)全球最佳老虎机平台,每日存款送3888元!
乐虎国际-乐虎国际官网-乐虎棋牌游戏官网-乐虎体育app下载(www.lhgjgw.com)真人百家乐连赢,最高88888,让您喜上加喜!
以上内容由千亿体育|千亿娱乐官网(www.qyylgw.com)整理发布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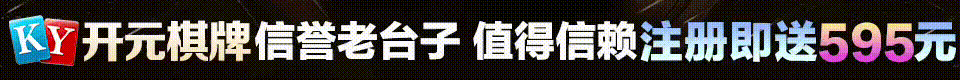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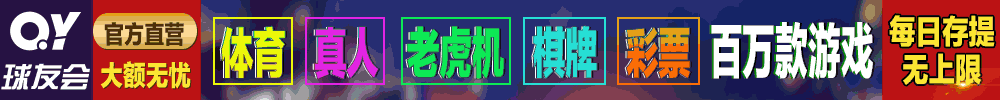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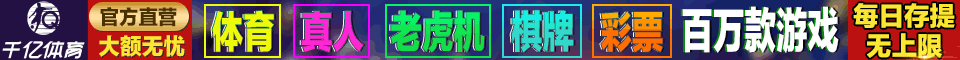




 佳心野核发力率队拿下RW!TTG 3-0 RW成功拿下关键一分
佳心野核发力率队拿下RW!TTG 3-0 RW成功拿下关键一分

